“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会前沙龙成功举办

为有效推动宪法学基础理论发展,在最根本的理论命题上促进学术商谈、论辩,“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系列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创新会议形式,设立会前论辩式沙龙,提炼出两组具有理论内在张力的学术命题,邀约持有不同立场主张的学者进行对谈,以期砥砺学思,求同存异,怀抱“知性的真诚”,共享“智性的愉悦”,增进学术共识与友谊。本次“会前沙龙”于7月16日下午云端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的二十余名学者,围绕两组学术命题展开了深入讨论:1.宪法的性质:规范性还是政治性?2.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基于效力还是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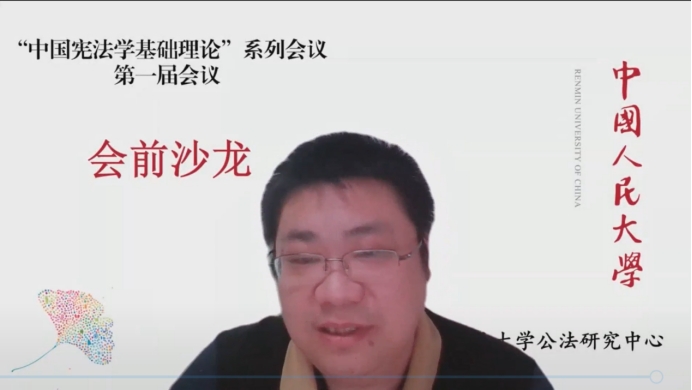
沙龙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旭主持并做致辞。王旭教授首先对各位嘉宾和观众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介绍了本次会议的召开背景。王旭教授指出,与正式会议相较,会前沙龙的交流环境更为轻松,但所议话题仍然承载着理性的深度。对“中国宪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首先应当从一些基础的判断开始,例如本次沙龙的议题“如何理解宪法性质与根本法地位来源”。法律固然带有实践性的面相,但实践本质上是由理论的世界观塑造的。历史学人讲“从常观变”:某种“变”是容易发生和观察的,但支配变化的“常”却是永恒回荡的执拗的低音,刺激着我们对实践具体命题的判断。当下中国正在推进的宪法实施,就无法回避关于宪法性质之判断的塑造。
第一组论辩命题为“宪法的性质:规范性还是政治性?”共有两名学者进行基调发言,八名学者展开对谈。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连泰首先以“中国宪法学的假辩论”为主题进行了基调发言。刘连泰教授认为,宪法的规范性和政治性之争,是宪法学研究长期争论的问题。但这是一场假辩论,因为如果将规范性和政治性视为对称的概念的两极,那么二者无法兼容。刘连泰教授指出,宪法的规范性是无须论证的,并围绕着宪法的政治性具体探讨了三点:1.宪法政治性的四个基本场域:立宪、宪法的规范密度、宪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宪法实施的非司法性;2.、宪法的功能在于把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为避免负面效应,只能以政治之外的宪法来进行规范,因此,宪法的规范性是宪法发挥功能的前提;3.需警惕用政治性来吞噬规范性,避免用政治的思维去代替规范的思维,警惕用需要代替宪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忠夏随后进行基调发言。李忠夏教授首先强调了宪法的规范性和政治性的特征不是并列的关系,并不能简单的等同。然后围绕着规范宪法学与政治宪法学来探讨宪法的属性,并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宪法的属性问题,也就是宪法的性质是什么;第二个是我国当前是属于宪法还是宪法法律,也就是该从法律意义还是时代意义的角度来理解宪法的性质。第三个问题是从更大的社会层面上来讨论部门宪法的属性问题,也就是除了宪法规范性和政治性的性质,还需要考虑宪法和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将三个问题结合成政治系统中宪法的运作限制以及社会限制的问题,并指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作为关于宪法性质的讨论的起点。最后他表明宪法的性质论从根本上而言还会涉及到法律系统自我运行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的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弘弘认为,首先,从宪法文本来看,宪法的政治性,是被输入的,其规范性是天生的。政治诉求或者体制上改革,需借助宪法的规范性来予以保障。同时,胡弘弘教授对规范性是本源的,政治是派生的这种表述进行了否定。其次,胡弘弘教授从宪法的历史发展角度对宪法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从宪法产生之处到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没有舍弃规范性这一内在属性。最后,胡弘弘教授指出,既有规范性又有政治性可能会模糊宪法的规范性。宪法的本质是规范性的,是以规范性为目的来作为体现它的政治性价值目标,需要警惕政治性性质分析的倾向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翟国强首先强调在借鉴具有普世性的理论以外,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国情来讨论我国所需要的宪法基础理论,并表明宪法的政治性和规范性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然后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阐明,如果从原则性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宪法是在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价值基础上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政治性和规范性的一致性。紧接着翟老师指出要基于宪法学的理论体系中建立起政治性和规范性的有机联系。然后指出如何从中国的语境来把握宪法和政治的关系是中国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最后强调在进行宪法哲学思考的过程中,要以我为主,立足于国情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学的理论体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泮伟江认为,宪法的政治性与规范性不是对立和孤立的两种性质,二者相互融合。泮伟江教授将政治分为初级政治和高级政治两种类型,高级政治可以借助宪法和法律得以规模化,因此宪法的政治性依赖于其法律性,而通过法律性使其政治性功能发挥到最大。同时,宪法在法律系统中承担的更多是次级规范的作用,它实际上是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形成的结构组合的产物,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相互发生影响也是通过这个机制来形成的。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练军认为可以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层面来理解宪法政治性和规范性之间的张力问题。首先,从时间的维度进行分析:在制宪的过程之中,宪法的政治性强于其规范性;而在宪法制定完成之后,其规范性则强于其政治性。其次,从内容维度进行分析:所有国家的宪法都存在着普适性跟本土性两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应通过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这样一个实践的维度来更好的体现宪法规范性。
南昌大学法学院程迈教授指出,从概念上说,政治性和规范性不是一对对立的概念,与规范性相对立的是事实而不是政治,而政治相对应的可能是法律而不是规范。政治和法律系统当然是有差别的,但还有共性,因为二者都处理一个共同体的共同的问题。政治系统需要规范性,但规范是一个主观价值判断问题,不同的主体可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能因为对政治系统所主张的规范的不认同推导出政治系统没有规范。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将中国和西方对立起来,我们需要把视野放宽,整个社会不只有政治和法律,也不是只有中国和西方,这样才能看到更多的共性,而不是差异。
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柳建龙指出,第一,就政治性和规范性问题,如果从不同的面相切入,一方面宪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另一方面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可以穿透历史,这种规范甚至来自民法,刑法或者其他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宪法的政治性和规范性应该是兼具的。第二,回到中国问题上,必须回答为什么要讨论宪法的规范性和宪法。如果宪法仅仅作为一种政治架构,讨论规范性或者政治性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把宪法作为法治的诉求或权利的保障书,政治性或者规范性就是判断一部宪法成功或者失败的重要标准。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屠凯提出了对八组范畴进行比较的分析框架。第一组范畴是宪法文本的形式化和非形式化,诸多宣誓性条款的非形式性可通过解释解决。第二组范畴是宪法内容的规范性到底关乎根本利益还是价值共识,但二者实质上应当是彼此契合的。第三组范畴是宪法研究立场的选择到底是一种意识形态判断还是一种学术探索。第四组范畴关于宪法话语到底是一种公共哲学还是一套专业话语,实际上更重要的还是作为一种再生产媒介。第五组范畴是宪法实施机关依靠法律机关还是政治机关,但二者区分是相对化的,毋宁说应依靠能够做出中立判断的机关。第六组范畴关于宪法的功能是维护权利还是解决政治纷争。第七组范畴围绕宪法现象到底是否属于政治活动展开,或许宪法现象存在不同于政治活动的底层逻辑。最后一组范畴关于宪法的对象到底是政治人还是法律人。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登杰提出了规范性和政治性相互成就的命题。一方面,规范性得益于政治性。宪法的规范性事实上来自于内含政治性的制宪权。正是这种政治性使得宪法成为实证法,但这里的政治性不一定是指一种经验现实,也可能是指一种内含规范性的理想状态。另一方面,政治性可以由规范性成就。一般而言,我们会去强调以规范性限制政治性,但是恰恰也是规范性给政治性提供空间。恰恰是实证化的宪法赋予了政治过程以正当性,人民意志只有通过宪法确认才会明晰。如果把规范性与政治性的关系落到宪法解释这点上,那么从宪法解释的效果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但这并不是法学研究对象。法学学者毋宁关注着宪法解释过程的规范性。
第二组论辩命题为“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基于效力还是内容?”共有两名学者进行基调发言,七名学者展开对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景辉在基调发言中提出,应当在区分效力和内容的基础上,从效力角度理解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在内容上只涉及部门法对宪法的具体化。宪法的根本法属性仅居于次要地位,最高法的效力是宪法成其为一部真正的宪法的最根本的属性。八二宪法序言中规定了宪法是根本法和最高法,其中包含了两个条件,第一个是基于内容的判断,第二个是双重因果关系。宪法在内容上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任务,所以是根本法;因为是根本法,所以是最高法。效力的判断不是最终的,而是基于内容的。另一种理解是合取式的,根本法和最高法是两个独立的判断,反对第二重因果关系,内容的判断和效力的判断相分离。对根本的正确判断是,根本与具体是对应关系。根本法是部门法的总则,部门法是根本法的具体化,因此宪法是是部门法总则,是法律总则、法律总论。根本法只有偶然内容,用以区别本国宪法和他国宪法,并使得以本国实定法为前提的宪法教义学研究成为可能。

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建学在基调发言中结合法国宪法发展史中根本法概念的渊源与演变,提出了对宪法根本法地位的四点思考:一是宪法根本法的地位,还可以从宪法审查角度来看,能够归入到审查依据的就是根本法,同时宪法的内容根本性、效力最高性与审查机制的有效性存在相互关联;二是根本法内含着规范主义思路,应避免主观性和取代制宪判断,理解根本法的含义要先看到“法”而不是“根本”,也不能把根本理解成内容重要,因为重要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文化的判断;三是根本法意味着宪法的一般性、抽象性和来源性(规范之规范),宪法派生出其他规范而不由其他规范派生,是规范的规范,决定着整个法律秩序存在的状态;四是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离不开审查机制的秩序维护功能,审查维持着由根本法到派生系统规范这一链条不同环节的秩序。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海平认为,对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讨论,需要明晰基本的方法论,或者置于特定的理论脉络中。对此,至少有三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是法哲学或法理学层面的应然思考,第二个是围绕宪法文本展开的教义学或释义学层面的分析,第三个是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考察社会现实中真正发挥宪法作用和效力的宪法内容的社会学视角。从纯粹法理学的角度,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可以同时基于内容和效力,既能够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同时又维护宪法文本本身的权威。八二宪法序言第十三自然段规定就是如此。宪法的内容和效力二者密不可分,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不能孤立地理解宪法的效力,必须结合宪法的内容,内容制约着效力。宪法规定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涉及到现代国家的建构,国体和政体的采用,国家结构形式的设置,这决定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也决定了其最高效力。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征认为宪法是否具有根本法地位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解读,即宪法往往从最根本的地方、用最根本的方法解决问题的。关于宪法是否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这一问题,陈征教授认为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制宪者是否有让规范发挥效力的意愿,二是这些规范写到宪法当中有没有发挥效力的可能。首先从宪法序言最后一个自然段来看,制宪者是有让宪法发挥最高法律效力的意愿,而序言和正文都是由全国人大统一通过在效力上不存在区别,所以制宪者是有让宪法全部规定、所有文字都发挥效力的意愿的;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宪法明确性不足就认为其难以发挥效力,宪法中的有些规定是持续指引立法活动的导向性规定,发挥的是指引效力而不是没有效力。陈征教授认为宪法中每一个规定发挥的效力可能不同,但是它们本身都具有法律效力,而且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郑磊从已发言学者的分歧中指出就根本法论根本法不够充分,提出将公法、母法的地位引入综合探究。将与谈题目为《宪法的三元基石地位》,主要阐述了四个递进的含义。第一,宪法既是公法,又是母法,同时更重要的是根本法,三者有相互交叠,但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统合而成的“三地位说”才能准确阐述宪法的地位。第二,关于宪法三元基石地位的中国理解包括两个维度。从经验维度看,以著名语录为例,比如说毛主席关于宪法的三个著名比喻――总章程、母法、根本大法正好分别对应“三地位说”。从规范维度看,《宪法》中出现“根本”的6处词频,正好形成一个串词定义:根本法就是规定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的法律。第三,三地位理论的发生逻辑和基本功能。例如,根本法对应的是一般法律和普通法律,效力是其区分标准,保证最高效力的是宪法保障制度;母法对应的是子法,区别标准是内容,实现机制是具体化、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或立法义务,陈景辉教授文章说的部门法总则是这个意义上的,而不是在以效力为标准的根本法意义上的;公法对应的是私法,这里的区分标准是界限,宪法在这个意义上是一道公权力和私领域之间的一道防火墙,对应机制是法的效力范围、调整范围。第四,作为舆论,连同前一单元讨论的宪法的多重意义上的政治性,同三地位理论有一个大致的对应关系,例如根本法赋予它最高效力,母法规定根本制度,这对应的是政治愿景、政治理想意义上的政治,这是“来赋予”、“来成就”政治权力;公法意义上,相对对应的是规范政治现实意义上的政治,是“来规范”政治的。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涛认为根本问题与最高问题应当区分,作为根本法的宪法和作为最高法的宪法,这两个命题之间有着密切的深刻的联系,但是它们不是同一个问题,应该分开处理。第一,根本法的属性和最高法的地位之间是因果关系,内容的根本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最高法的地位的理由。第二,内容和效力是彼此分开的命题,不同的形式它们的效力是不同的。第三,现代宪法的一个出发点是宪法立下了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使我们认为有必要把这个文件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不能被轻易侵犯、废弃或绕开,这本身就证明内容的重要性可以支撑最高地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小建从宪法内容的根本性与效力的最高性二者的关系层面进行了阐述。他认为,这两者之间虽具有直接对应关系,但也并非完全一致。二者存在直接对应关系,主要是从宪法的本质去理解,宪法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基本组织框架的规定和对社会多元价值的整合,这个功能是其他部门法替代不了的,由此决定了宪法的最高法效力;二者并非完全一致,主要是指宪法所规定的部分内容,其他低位阶的部门法对此也有所规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其他低位阶部门法也属于根本法,内容的根本性不能当然推导出效力的最高性。最后,他认为,正是宪法对社会价值的持续整合以及对国家目标和使命的规定,构成了宪法内容更新的源泉,而合宪性审查只是其中的机制之一。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楠从宪法序言文本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宪法序言的第十三自然段是从四个不同的维度对宪法的性质进行了描述,即宪法的规范性、宪法内容上的特殊性、宪法的根本性以及宪法法律规范上的最高性。基于此,她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宪法的根本法效力实际上是源自制宪者的决断,这是根本法产生的主要因素,并且从横向与其他国家宪法比较、纵向回顾新中国制宪史的角度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解释。最后,她总结道,宪法序言的第十三自然段从四个维度描述的宪法性质是一种并列兼统合的关系,很难区分开,以此产生国家刚性。宪法根本法的实践方面,除了宪法宣誓之外,救济机制以及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众认同都是不可或缺的。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陈明辉认为,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的区别主要有三点:一是研究旨趣的不同,政治宪法学可能更倾向于一些国家理论,包括政党、代表、主权等等问题;二是价值立场的不同,政治宪法学更倾向于一种国家主义,而不是中立的或者是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三是对规范的理解不同,政治宪法学更关注那些不能够被司法化的宪法内容和宪法的核心问题,即认为这些东西只能由具备宪法素养的政治家来作出最终的决断。同时,陈明辉教授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结合英国宪法史中根本法概念的阐发过程和消亡过程,提出在中国语境之下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法效力需要本土化的理论建构。要警惕对宪法的形式化、单点化和空洞化的理解。应当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对宪法的实质内容进行更基础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让宪法的应用技术和应用制度得到充分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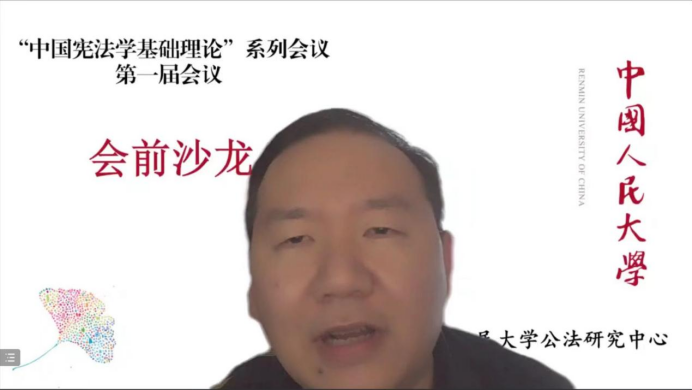
沙龙总结环节,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锴做总结发言。王锴教授首先对各位老师的发言作了简短概括。对于第一单元主题,王锴教授认为宪法主要还是规范的,但是它跟政治相关,会调整政治活动。而宪法能不能彻底的解决政治上的纷争,是存在争论的,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国情来确定,我们强调的政治文明就说明了宪法作为政治的一种框架秩序决定了政治活动只能在宪法设定的边界内享有一定的裁量权。此外,王锴教授认为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制宪权的问题,制宪权决定着到底是政治来决定宪法,还是宪法来决定政治。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宪法到底是规范属性占优还是政治属性占优可能是日后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对于第二单元主题,即根本法到底是内容还是效力的问题,王锴教授认为内容和效力可能是两个问题,应当分离的去看待。在这个问题上,宪法的根本法属性怎样得到保障,使之成为真正公认的根本法,是未来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
王旭教授最后代表主办方感谢与会各方的莅临和支持。他表示,虽然会议形式受限,但今天的沙龙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主办方也将继续努力做好今后的组织工作。随后,王旭教授宣布沙龙圆满结束。
文章来源:明德公法网 发布时间:2022/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