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3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成功举办
2020年7月1日,值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之际,为回顾“一国两制”的实践历程,总结“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展望“一国两制”的发展前景,由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香港紫荆研究院、《法学评论》编辑部共同协办的“香港回归23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线上成功举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多位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另有30多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和学生在线旁听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所长、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韩大元教授主持,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致辞。
韩大元教授指出,2020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23年前的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项重大贡献。回归23年来,国家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一国两制”的精神和原则,始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为确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一国两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是在实践中也遇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过去一年多以来的修例风波,向所有关心“一国两制”的人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建立健全维护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推动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
韩大元教授指出,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制定,是坚持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重大举措,体现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有助于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也有助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在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守“一国两制”的初心,更加珍惜“一国两制”所取得的成绩,客观地正视“一国两制”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新课题,使“一国两制”这一承载中国人民智慧和历史使命的制度创新,继续保持它的生命力。
随着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香港将会继续保持法治、开放、国际化等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对国家的改革开放将会继续做出她的独特贡献。我们要站在新的更加全局更加宽广的历史视角,来回顾23年以前的香港回归,以及香港回归23年来的历史事实和伟大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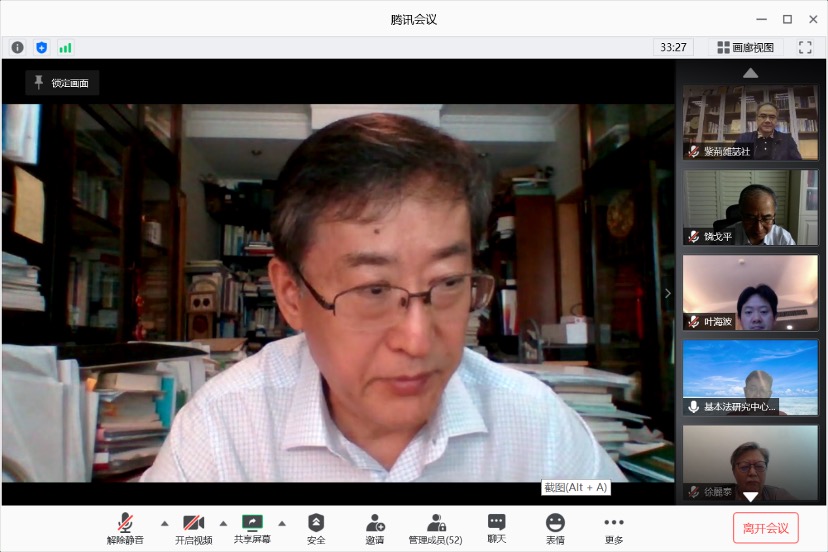
王振民教授在致辞中指出,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问题意识是,既为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保障“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也为维护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国家的安全。因此,国家层面的国家安全立法必不可少。
王振民教授指出,全国人大在《决定》中明确,它是直接根据宪法作出了《决定》,符合基本法的原则精神和框架结构。整个《决定》加上立法,是基本法的必要补充和发展完善,是基本法的延伸,而不是在基本法之外“另起炉灶”。王振民教授强调,香港国安立法的整个制度设计经过精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论证,它的合宪性、合理性以及正当性是非常扎实的。
王振民教授认为,香港国安立法的关键内容就是四个词:一是“国家层面”,也就是从国家层面来开展工程,而不是特区层面;二是,“建立健全”,也就是有些是基本法或香港本地法律的规定中已经有的而需要健全的,还有些是新设的;三是“法律制度”,也就是要弥补基本法和香港本地法律当中有关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些实体法的缺失;四是“执行机制”,也就是特别强调中央和特区两个层面的执行机制。
王振民教授最后指出,与国际经验比较,香港国安立法是最低程度的、最低标准的保底做法,是最低立法。与外国的国家安全法律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香港国安法要宽松的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将内地的国家安全法直接在香港实施。因此,香港国安立法恰恰是为了挽救“一国两制”,保住“一国两制”的底线,让“一国两制”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第一单元
会议第一单元为主旨发言环节。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女士、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先生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北京大学法学院饶戈平教授、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郑陈兰如基金宪法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先生先后发表主题发言。
范徐丽泰女士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香港回归祖国23年,这23年并非风平浪静,而是波涛汹涌。时至今日,香港这一条小帆船已经慢慢地变成游艇,而我们身后的祖国已经是航空母舰,遨游四海、无惧风浪,将小船紧紧地连接于祖国这艘大船的纽带就是“一国两制”基本方针。为什么这么说呢?她跟大家分享了几则故事:一是围绕1999年初香港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做出的判决,以及后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释法的有关争议;第二,关于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争议;第三,关于2005年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的争议。第四,关于香港特区的政制发展的争议。
范徐丽泰女士认为,要保障“一国两制”,要让基本法全面准确的落实,要令香港市民安居乐业,就必须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和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些都要让香港的市民,尤其是青年人知道。香港市民要相信祖国不会害香港,若不是想“一国两制”成功,何必努力地准确落实基本法,这些事情都是需要长期的教育和不断的宣传解读。范徐丽泰女士强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但我们一定要开始去做,因为如果不开始去做,难道看着香港沉下去吗?我想我们是没有选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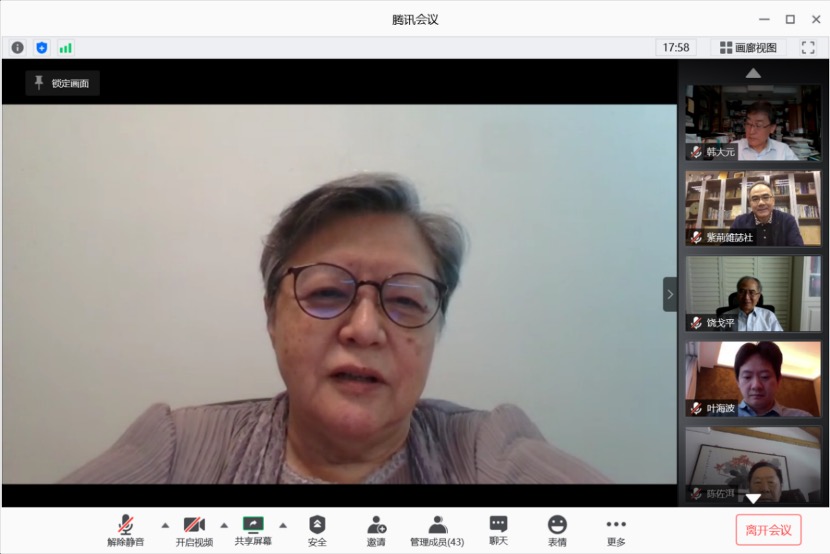
陈佐洱先生在主旨演讲中首先给大家分享了他亲自参与香港回归的那段不平凡的历程,包括中英谈判的一些历史事实,以及参与制定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过程。随后他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管治权和对香港事务的主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中央的手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染指,这是我们坚守的一条底线。陈佐洱先生指出,回顾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的23年,波澜起伏,史无前例,我们一路捍卫着百多年来争取香港回归祖国的硕果,在斗争中成功地丰富和发展着“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谱写了崭新的篇章。陈佐洱先生强调,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让香港回家的斗争史不应该被遗忘,尤其应该真实地写进香港青少年一代的历史教科书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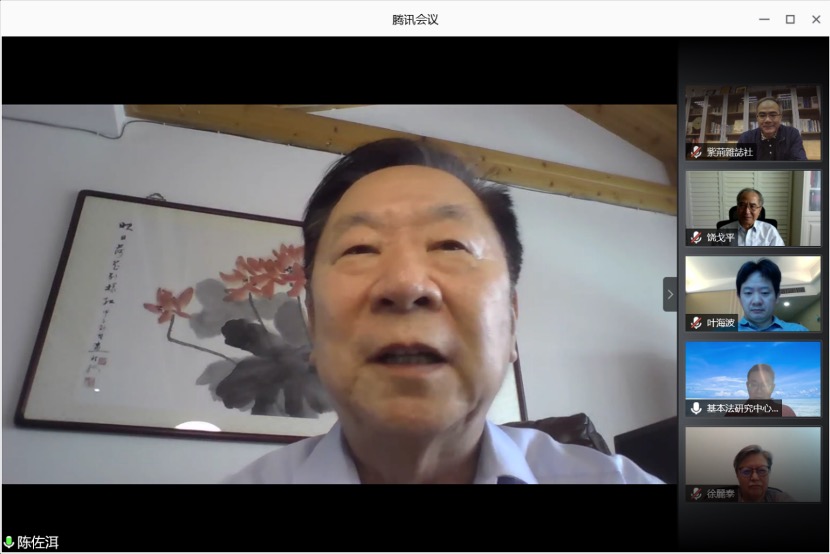
饶戈平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主要谈了对当前香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他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的同时,在繁荣稳定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深层次的矛盾,这些深层次矛盾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香港社会本身固有的问题,是回归以前本已经存在的问题;另一类属于“一国两制”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饶戈平教授指出,各种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一国两制”的问题,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香港的问题。而香港永续生存和繁荣稳定的土壤必须是也只能是中国大地,只有国家和内地才真正把香港的安危兴衰放在心上,从而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所以从大局来看,“一国两制”不单是保障回归到香港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国家内地和香港之间最大的政治共识,最大的利益公约数。
饶戈平教授指出,中央是“一国两制”的制定者,实施的主导者,掌控“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香港社会主要矛盾的妥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国家靠中央层面,只有中央才有权威,有能力指引和保障“一国两制”行进宪制轨道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地实施“一国两制”,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坚持中央对实施“一国两制”的主导权和掌控权;必须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同香港高度自治权的结合;必须坚持严格按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成“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必须坚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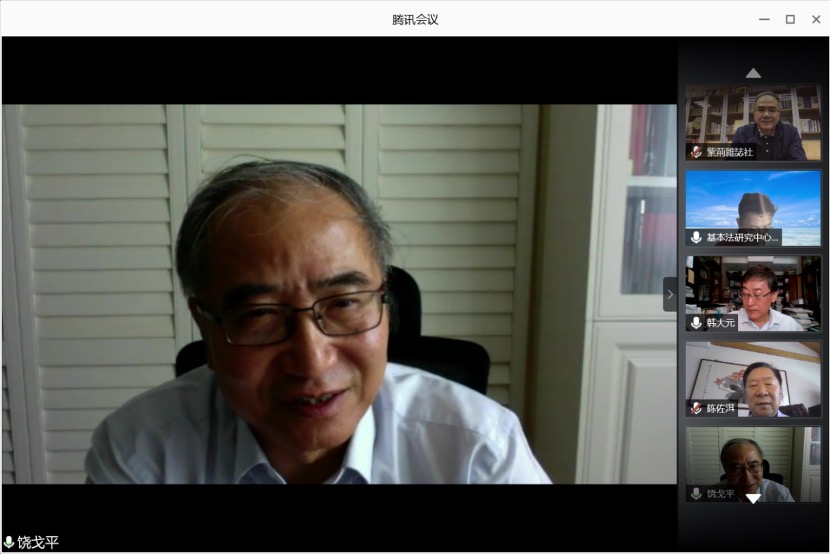
陈弘毅教授在题为“香港基本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政法争议”的主题发言中指出,香港基本法实施过程之中的政法争议,从九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反映了人们对于基本法的一些不同的理解和解读。反对派对于基本法提出的一些另类的解释,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一直存在,不断发展,而且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去年的反修例运动是反对派对基本法的另类理解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表现。
陈弘毅教授指出,香港基本法作为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具有不同于民商法或者其他法律的高度政治性。对于基本法的解读,有一种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解读,即坚持“一国两制”里面的“一国”原则的重要性;还有一种另类解读,即试图降低“一国”的成分,加强“两制”的成分,使高度自治变成完全自治。从基本法的制定或实施以来的各种重大的争议看,我们都可以看到对基本法不同的解读。陈弘毅教授详细回顾了以下围绕香港基本法出现的八次政法争议:一是,97年香港回归之初,关于临时立法会是否违反基本法的争议;二是,1999年关于人大首次解释基本法的争议;三是,2003年关于基本法23条立法的争议;四是,政制发展过程中关于基本法第45条等条款的争议;五是,2016年关于立法会议员违法宣誓引发的人大针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的争议;六是,2017年关于人大“一地两检”决定的争议;七是,2018年关于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争议;八是,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香港进行国家安全立法所引发的基本法第23条理解的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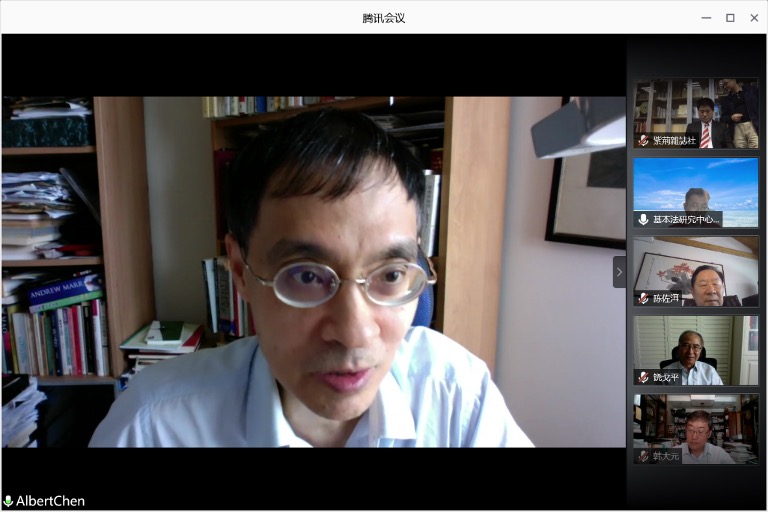
第二单元
会议第二单元为专家与谈环节,由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一国两制”法律研究所秘书长黄明涛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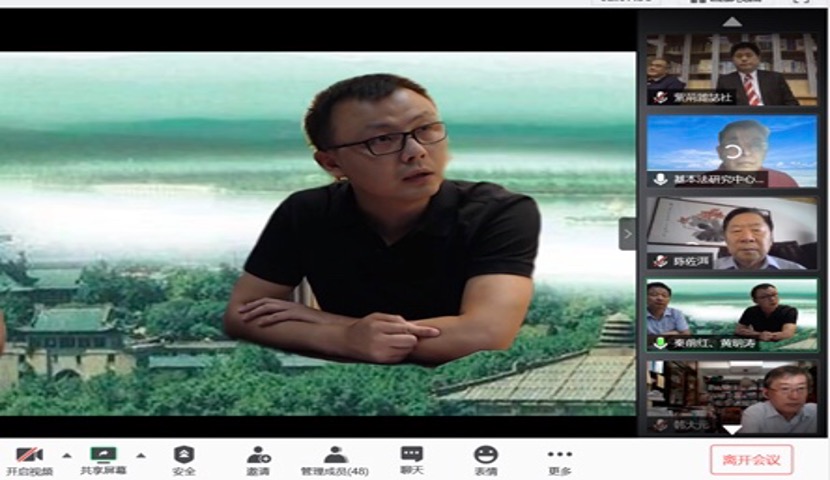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邹平学教授以“香港基本法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以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的论著为视角”为题,主要从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的研究概貌、香港基本法研究的总体评估和香港基本法研究的未来展望这三个方面对香港基本法的学术研究进行整体性的概括和反思。

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院教授陈端洪指出,在‘一国两制’实践经历整整23年以后,有必要进行真正的反思,他认为,“一国两制”方针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共存,存在“二律背反”现象。这些现象要求我们反思如下问题:如何界定香港的宪法和法律地位?如何界定港人身份?自治权如何行使?陈端洪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立法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方式。

《紫荆》杂志社社长杨勇先生在主题为“中央政府驻港机构遵守香港当地法律有关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中央驻港机构及其人员除了遵守全国性法律是不是应该遵守香港本地法律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涉及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实施、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和中央驻港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如何更好地履行法定职责。他认为,第一,必须明确回归以后依据基本法,中央政府延续了回归前英国官方的一些权力;第二,现行法律对中央驻港机构是不是要遵守香港当地法律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三,中联办要遵守香港当地的法律,这是中央政府对授权机构的纪律性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李树忠教授在主题为“以更高的智慧来实践‘一国两制’”的发言中指出,“一国两制”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困境,未来我们应该用更高的智慧去实践“一国两制”。这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用更高的智慧安放不同制度之下的意识形态在“一国两制”当中的位置;二是,用更高的智慧开展特区民主实践;三是,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解决“一国两制”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四是,以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为契机,为“一国两制”的实践创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指出,基本法研究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问题至今都未解决。基本法作为宪制性法律具有高度政治性,基本法研究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治与法律、政治与学术的问题,基本法研究的学术发表和学术生长的困难,基本法研究对学术背景提出的要求等都对良性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的形成产生了窒碍。秦前红教授强调,未来的“一国两制”发展和香港的繁荣稳定,有赖于稳定的学术队伍和客观的学术研究的支撑,因此要给予学者适当的学术研究空间。

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朱国斌教授以“不忘初心 实践‘一国两制’”为题分别从历史、现在和未来三个维度研究观察了“一国两制”实践和基本法实施。他认为,从历史维度看,基本法体现并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对香港未来的共识、利用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未来所作的安排,以及希望香港继续为国家的繁荣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的期待。从现实维度看,“一国两制”实践存在在港信心不足、“爱国者治港”面临挑战、政治秩序乃至宪制秩序面临挑战以及建制派和反对派渐行渐远等问题。针对未来如何在香港正确贯彻“一国两制”,朱国斌教授认为,应当坚守“一国两制”、回归基本法文本,保证中央管治权与保障特区自治权,重建两地互信、弥合社会裂痕,摒弃仇恨对立、回归理性务实,以及适时重启改革、渐进推进民主。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在主题为“香港国安立法再次证明中央坚持‘一国两制’”的发言中指出,香港国安立法体现维护“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初心;香港国安立法比较好地兼顾了“一国”与“两制”,兼顾了既要保障国家安全又要尊重和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兼顾了中央在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香港国安立法秉持一种敢于创新的精神,国安立法是立法方面的创新,是一国两制和制定基本法的继续创新,是成文法和普通法相结合的创新,是组织法、实体法、程序法相结合的创新。在未来国安立法实施中遇到新问题、新挑战,要继续秉持创新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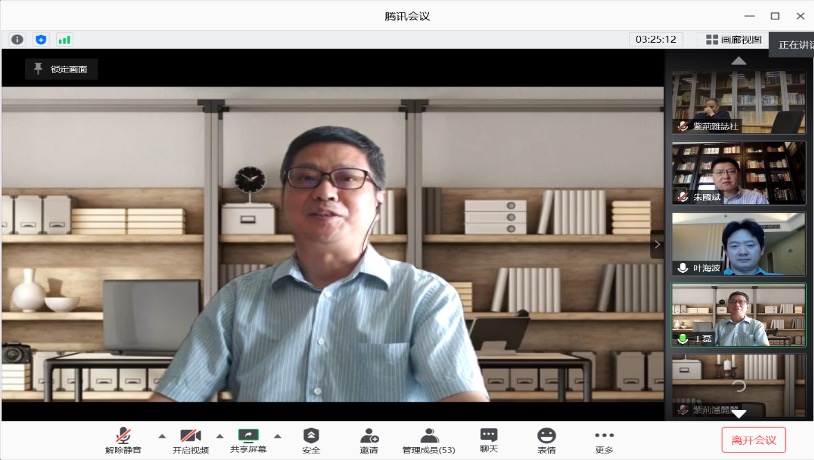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陈欣新研究员指出,“一国两制”,前无古人,越是在实践中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越应该回顾和总结香港回归23年来“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成功经验,这有助于未来“一国两制”的长远稳定发展。“一国两制”目标不仅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也要求把香港特区建设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体系,而且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不应是畸形的。他认为,应尽最大努力去平衡“一国两制”中“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尽最大努力去维护国家安全同时又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深圳大学法学院叶海波教授指出,在1982年宪法修订时,港澳没有回归,最终的方向是在社会主义的整体下容纳资本主义制度,但两种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是绝对对立的,可能走向互相否定的一面,这让中国进入紧急状态。因此,1982年宪法实际包含着一个紧急条款,即第31条,自身也具有紧急宪法的本质属性。只要进入紧急状态,第31条就会反复启动。基本法制定的目的就是通过商谈过程形成基本共识来化解这种紧急状态。外部对香港的干预和香港本土分离主义运动打破了基本法中的基本共识,进而又触发了第31条,中央认为进入了一种为生存而战的紧急状态,希望人大决定、香港国安立法和基本法一道,让中国回归常态法治。叶海波教授提出,在立法完成后要遵循“基本法穷尽主义”的原则,这包括三项内涵:一是主张在基本法和宪法的关系上,既要维护宪法至上的绝对性,也推定基本法的自足性和体系性;二是香港管治应该穷尽基本法上的机制,不轻易援用基本法外的权威来源;三是首问负责制。基本法和港区国安法将香港治理的法定责任课予特定机关,这些机关是法定首问机关,必须积极履行职责承担首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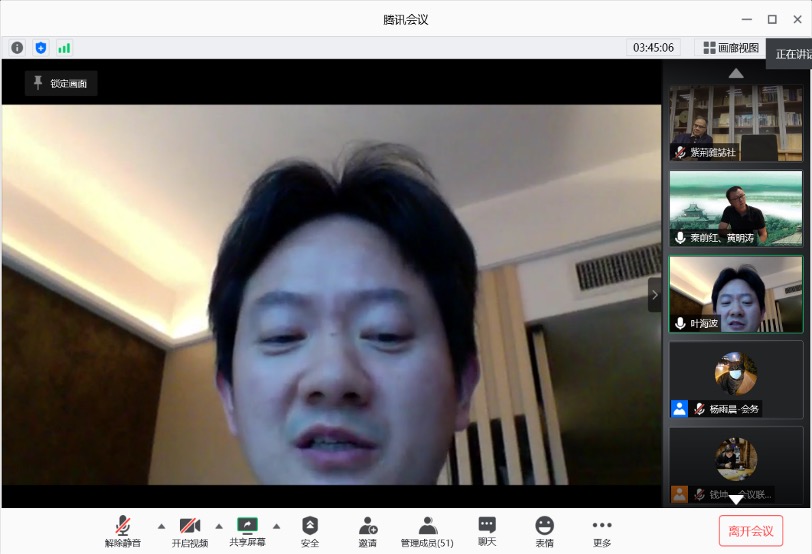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夏正林教授指出,香港国安立法在特别行政区正式生效后,如何真正落地实施将是一个问题,下一步应尽快制定国安法实施指引。夏正林教授认为,香港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民生和经济发展问题,香港特区下一步还是应该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向内地靠拢,利用国安法实施所带来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彻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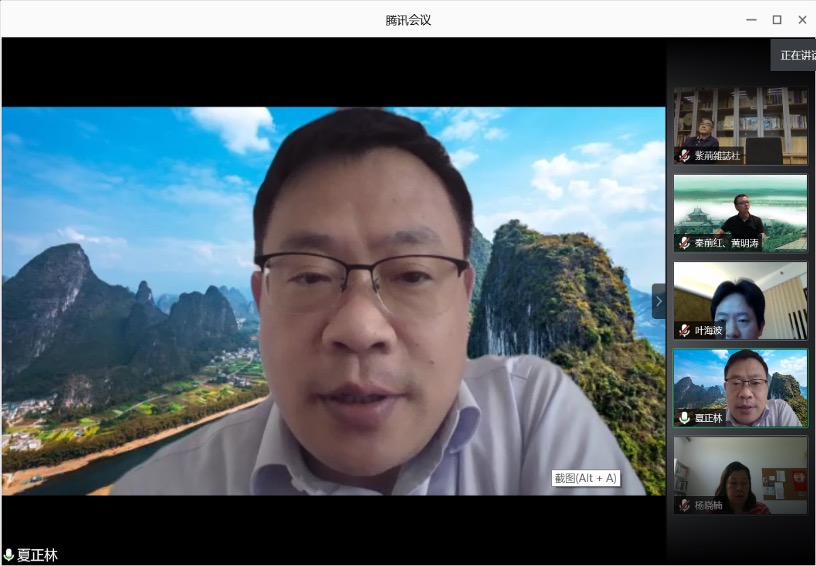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杨晓楠教授指出,应该始终相信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之一,基本法保障了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国两制”实践中面临的一些问题不应该归因于基本法,人们也不应动辄质疑基本法,而是要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努力创造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杨晓楠教授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维护香港秩序的前提,如果没有国家安全的话,那么也不能想象一个城市的安全和秩序是可以存在的。但法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香港居民的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持城市的稳定与秩序,最终是为了保障香港居民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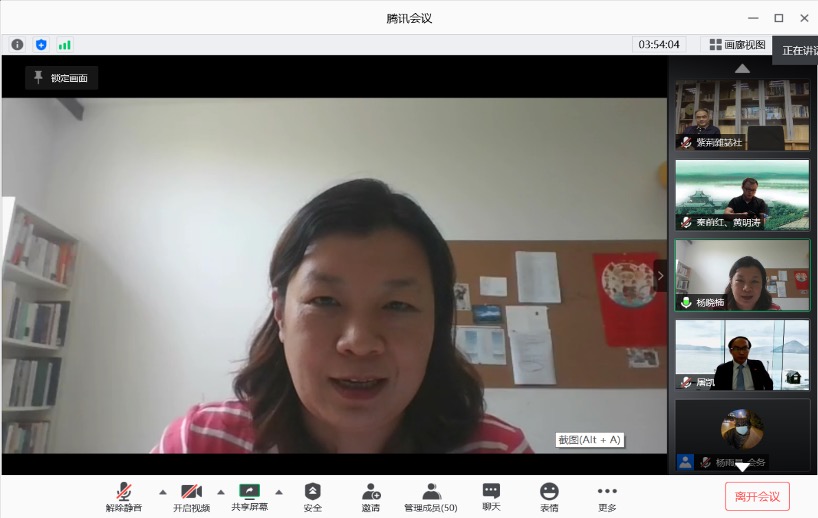
清华大学法学院屠凯副教授指出,重温邓小平先生就“一国两制”发表的几次重要讲话,重新思考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很有意义的。屠凯副教授认为,邓小平在就“一国两制”发表的几次重要的讲话中创造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概念的两种不同的语境,在这两种语境里面,他对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各有不同的强调的。在1984年会见香港工商界人士的这次讲话里,邓小平是在内地和港澳关系的语境中来讨论社会主义的,而在1984年会见香港同胞的国庆观礼团的讲话和1987年会见基本法草委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在中央和特区的关系的语境中来阐述社会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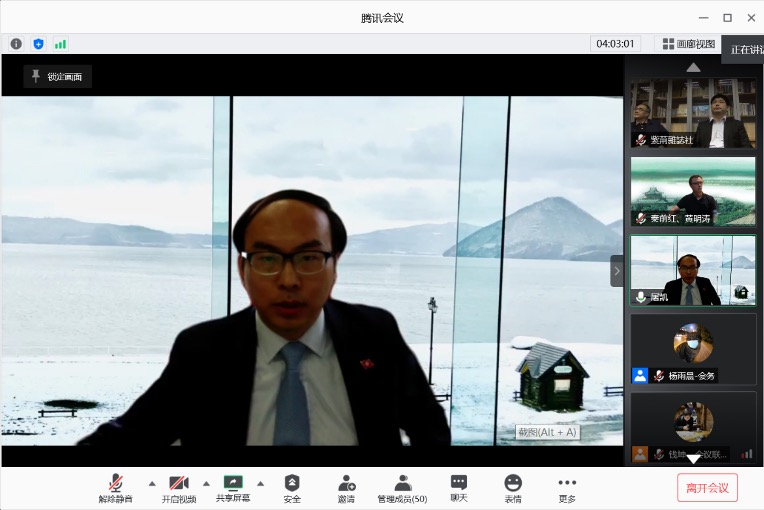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田飞龙副教授指出,“一国两制”无论是政策、理论、战略还是制度,都是由中国主导,是整个中国现代化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研究不仅要求学者具备能够对普通法或者香港本地进行法律分析的基本知识,而且其实还要熟悉国家法律的整体走向,更要了解香港作为中美关系或者战后国际法秩序一部分这样一个动态的结构性变迁。这就要求学者在做港澳研究的时候要进行适当的学科多元化和方法多元化,同时也要让纯粹的法学条文主义和政治宪法学或者其他的研究路径相得益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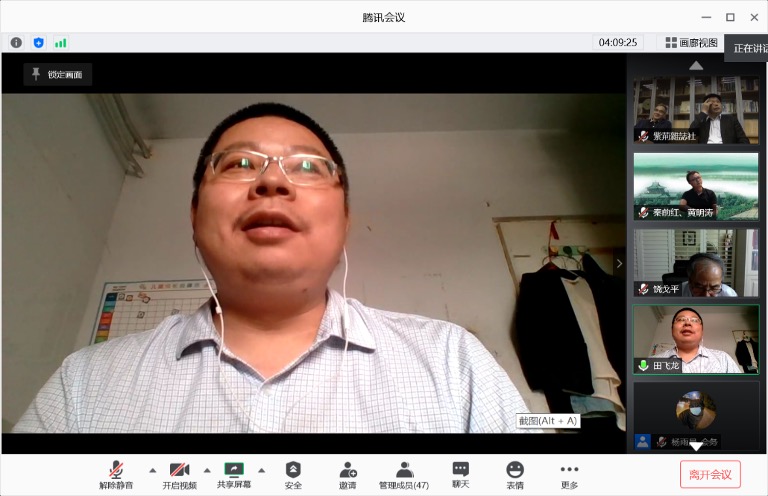
会议总结暨闭幕式
在会议总结暨闭幕式上,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署理院长傅华伶教授指出,香港国安法已在香港实施,香港作为法治社会,相信会严格遵守这部法律。但也不要低估这部法律对香港社会心理的影响。目前很多人对这部法律仍有疑问甚至批评,多数人的批评是善意的,这些声音不应当被压制。香港国安法的总体制度已经确立,但在实施过程中仍有许多细节需要解决,应加强与香港社会各方面的沟通,使港人的意见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反映,促进这部法律的顺利实施。
香港国安法有利于香港恢复稳定的社会环境,但“一国两制”在实施过程中还有许多其它问题,单靠香港国安法无法完全解决。中央既已发挥主导作用,可进一步考虑如何引导香港在政治上实现良性地变化、完善特区施政、增强港人对特区政府及“一国两制”的信心,在国安法实施后再行改革。香港是个复杂的社会,由不同理念、不同阶层的人群组成,有必要仔细考量香港社会民情的各个方面,在法律和政策制定上,应从香港现实出发。香港国安法证明,即使如此重大的危机,仍然能够在基本法框架下解决,宪法和法律仍是各方遵守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