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及其规范解析
关键词:国家性质 政体 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
作者简介:门中敬,法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司法研究所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1]坚持宪法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不动摇,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实施宪法的必然要求。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有丝毫动摇”“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2]要求,应当在规范意义上展开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内涵和规范价值的研究,以期在制度规范层面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为构建中国自主宪法学知识体系提供学理助力。
一、国家性质的宪法表述语辨析
我国自清末颁布第一部成文宪法《钦定宪法大纲》以来,大体颁行过17部宪法性文件。[3]这17部宪法性文件无一例外都在第1条规定了国家性质。其中,封建帝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国家性质为帝国,[4]民国时期的宪法性文件规定的国家性质为民主国或民主共和国,[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宪法性文件,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是“无产阶级专政”,[6]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7]权威观点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5部宪法性文件虽然在国家性质的表述语上存在差异,但在内涵上基本一致,本质上并无不同。如龚育之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致的;[8]刘山鹰认为,1954年《宪法》规定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在其内涵上与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一致,只是少了“专政”。[9]但是,即便在政治内涵上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两者在表述语尤其是限定语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表述语上的差异
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在表述语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没有明确提及“无产阶级”,而是强调“人民民主”,后者则直接明确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地位。由于“人民民主”也是由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以在政治内涵上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国家性质的表述背后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在阶级还存在的社会,[10]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是如何既“专政”又“民主共和”的?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共和国是不同于西方民主共和国的,并创造性地将其命名为“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国家[11])。
“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权理论和政治表达习惯,但与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政体理论明显不同。按照16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布丹(Jean Bodin)在《国家六论》中提出的政体理论,政体的形式因主权的归属而有所不同,一人掌握主权的称之为君主政体,主权归少数人掌握的称之为贵族政体,主权归多数人掌握的称之为民主政体。[12]按照我国的人民主权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纳的也是一种共和体制,这与让·布丹的共和政体理论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是,按照我国现行1982年《宪法》第1条“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规定,以及按照我国的政治表达习惯,人民民主专政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本质,体现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因此,我国的国体理论是一种体现阶级属性的共和理论。
这也可以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国体和政体是分开的?据学者考证,国体和政体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是伴随近代西学东渐而演变的一组政治学概念,其传入是外国来华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共同努力的结果,经历了概念传入、认识模糊、认识逐渐清晰和本土定义四个阶段。国体和政体二元论出自日本学者穗积八束,后被梁启超所采纳。[13]毛泽东阐明了国体和政体概念的本土定义。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14]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15]
从毛泽东关于国体和政体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表述,主要解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而解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则由政体来解决。但无论如何,相较于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已经内含了“人民民主”这一政权构成的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下文讨论的国家性质在表述上的限定语差异中,可以更加明显地观察到两者的差异。
(二)国家性质在表述上的限定语差异
详细解读1949年《共同纲领》第1条可以发现,“人民民主专政”有一个重要的限定语:“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这里的各民主阶级,按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的观点,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毛泽东出于吸收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国家政权以发挥其积极作用的目的,不再强调马克思所秉持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6],而是将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了“人民”的范围。另据学者考证,从中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的沟通情况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一直重视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解释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认为“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东欧的人民民主制度相比,在阶级属性上,人民民主专政虽然也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却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合作对象,作为政权的一部分;在政治制度上,中国坚持多党合作,并且有资产阶级政党参与其中;在具体政策上,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既利用也限制,支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的发展。”[17]例如,1951年5月1日《人民日报》曾刊登彭真《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中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一文,强调“今天中国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为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革命联盟,所以它既不是代议制,也还不是苏维埃制,而是人民代表会议制。经验证明,这是中国现阶段最好的政权形式”。[18]尽管其后毛泽东在会见米高扬时提到“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其后,毛泽东并没有重复这样的说法。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1954年《宪法草案》全国政协宪法草案座谈会的讨论中,有如下意见或建议:“为什么在宪法草案中未提到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议在第1条中加上‘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第1条‘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下面’下面加‘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第1条‘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下面加‘社会主义性质的’或‘劳动人民的’或‘各民主党派参加的’”。[19]在1954年《宪法草案》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讨论(纪要)中,亦有以下归纳意见:对第1条,“归纳起来有3个意见:……(3)地方上有的主张加‘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20]。对此,韩大元指出,从《共同纲领》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到1954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国家”性质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变化而出现的。[21]也就是说,这种表述语上的变化,反映了当时的阶级结构变化,并非可有可无。
事实上,及至1953年公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中国共产党才宣布“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22],其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才揭开了人民民主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转变的序幕。此后,党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也日渐增多。如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等,均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23]可见,强调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是基于“三反”“五反”运动的需要,目的在于强化通过阶级斗争手段,实现改造资产阶级的目标,而非宪法规范意义上的表述。因为,在规范意义上两者是无法做到一致的。尽管现行1982年《宪法》序言第6自然段中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但这一表述并不能说明,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与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规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规范内涵上相同。因为,1949年《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序言规定的统一战线构成虽有一定差异,但都包含有“民主阶级”或“民主党派”的表述,[24]但在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中,并未出现“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表述,这并非巧合。
综上分析,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在表述上的限定语差异,在于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在国家地位上的差异。但是,在政治内涵上,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或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因而毫无疑问,在政治内涵上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正如下文分析指出的,并不能由此否认两者在规范内涵和规范价值上的差异。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内涵解析
要解析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首先需要解释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由于人民民主专政是由“人民民主”和“专政”结合在一起的词汇,而“人民民主”则是由“人民”和“民主”结合在一起的词汇,故而应当对宪法上“人民”“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内涵进行解析。
(一)人民和人民民主的宪法规范含义
1.人民的宪法规范含义
在现代民主国家,一切公共权力都是从人民这个合法性原点派生的。[25]我国自有宪法以降,在宪法文本中最早出现“人民”一词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前的《钦定宪法大纲》用的是“臣民”。《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第4条规定:“凡依法律所定属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人民。”这里的“人民”,显然与今天宪法中的“公民”含义相同,该含义一致沿用到《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至《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才以国民代之,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凡依法律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26]
由是观之,民国时期宪法文件中的“人民”,在涉及主权之所在时,多用“国民全体”一词;在涉及具体的权利与义务时,多用“人民”一词,其含义较类似于当前语境下的公民一词。[27]与民国时期诸宪法不同,新中国的宪法性文件在涉及主权之所在时,多用“人民”一词;在涉及具体的权利与义务时,多用“公民”一词。而且,“人民”与“公民”并无整体与部分的逻辑关系,且随政治发展阶段的不同,宪法中“人民”的含义和范围也发生着剧烈变动(见表1)。
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部宪法性文件序言中的“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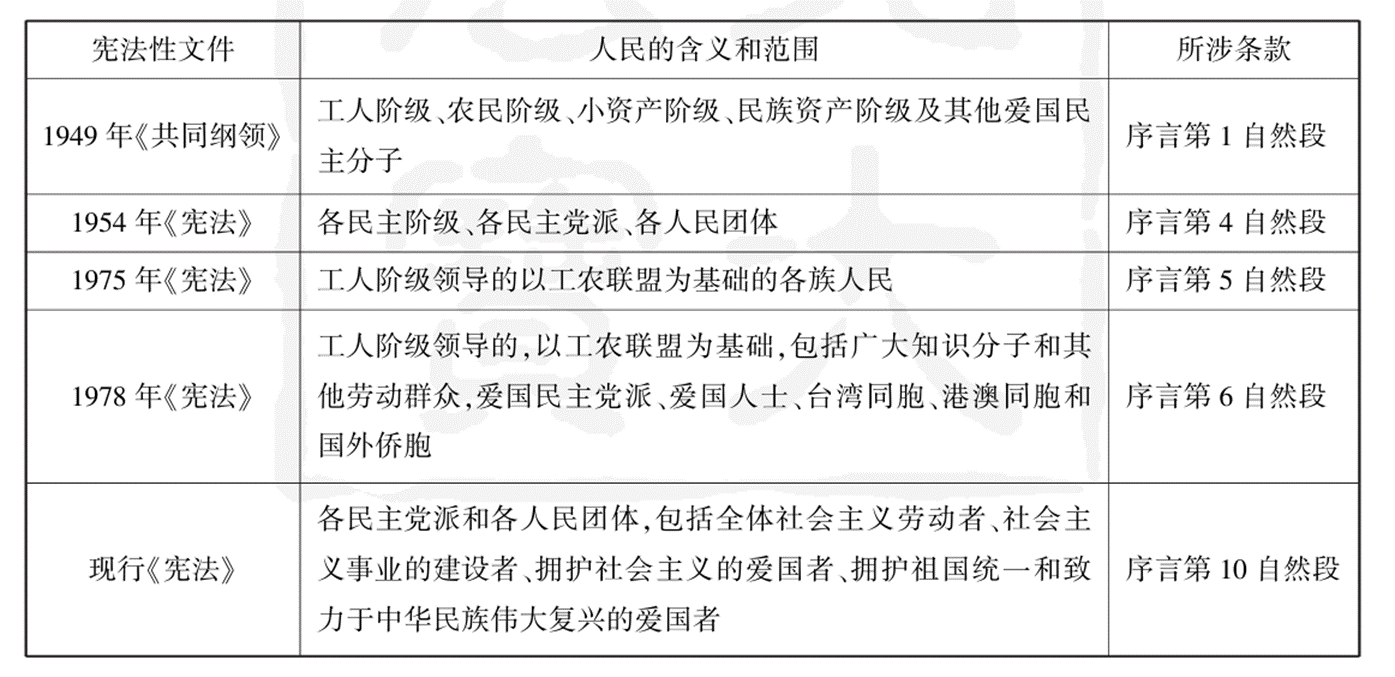
从我国历部宪法性文件序言中“人民”的范围变动及其表述上的变化来看,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通过明确“统一战线构成”的方式,区分人民和敌人,尽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多个宪法性文本中并没有对人民的概念加以定义,而在另外一些重要场合,制宪者对“人民”一词的说明,则不断加深了“人民等于统一战线构成”的观念。[28]据此,杨陈在对宪法文本中“人民”的七种用法[29]作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后指出:“就每一种用法自身而言,都有其正当的理由存在。但如果把这七种用法叠加在一起就难以形成一个内在融通的意义体系,甚至在有些用法之间,如果不加以适当的解释则是相互矛盾的。而这对于宪法学体系和宪法秩序都是难以接受的。”[30]而且,到目前为止,现有研究并没有能对“人民”这一概念作出一个内在融贯的定义,也没有能充分回应因“人民”一词本身的歧义产生的诸多争论。
“人民”一词本身的歧义产生,是对其政治含义的解读以及政治话语的模糊性决定的。对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来说,“人民”的范围问题无法通过宪法序言中的“统一战线构成”这一政治内涵获得明确答案。在规范意义上,人民的范围如何体现其法律效力和具备可操作性,更为重要。从宪法规范层面来看,人民的范围与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的享有和行使有关,因为,宪法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作为制宪者的人民赋予个体公民的权利,而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来自作为制宪者的人民,因此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整体授予作为个体的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权力)。
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力在现行1982年《宪法》上的规范依据是1982年《宪法》第2条,该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根据该条规定,现行1982年《宪法》明确了哪些公民属于人民,哪些公民不属于人民。因为,不属于人民的公民无法获得“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政治权力,自然也就不能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如果结合1982年《宪法》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31]之规定,毫无疑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规范意义上,我国宪法上的“人民”并不包括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5部宪法性文件中,与宪法序言中“人民”的范围差异相对应,人民或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条款规定同样存在较大的差别(见下页表2)。
从下述宪法性文件的比较规定来看,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了人民而非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另外4部《宪法》皆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限制来看,4部宪法除了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限制条件,1954年《宪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是“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1982年《宪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可见,5部宪法性文件规定的人民或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限制性条件并不相同。比较而言,现行1982年《宪法》的规定更加明确具体,更加有利于保护公民的民主政治权利。[32]
表2 历部宪法性文件中“人民”“公民”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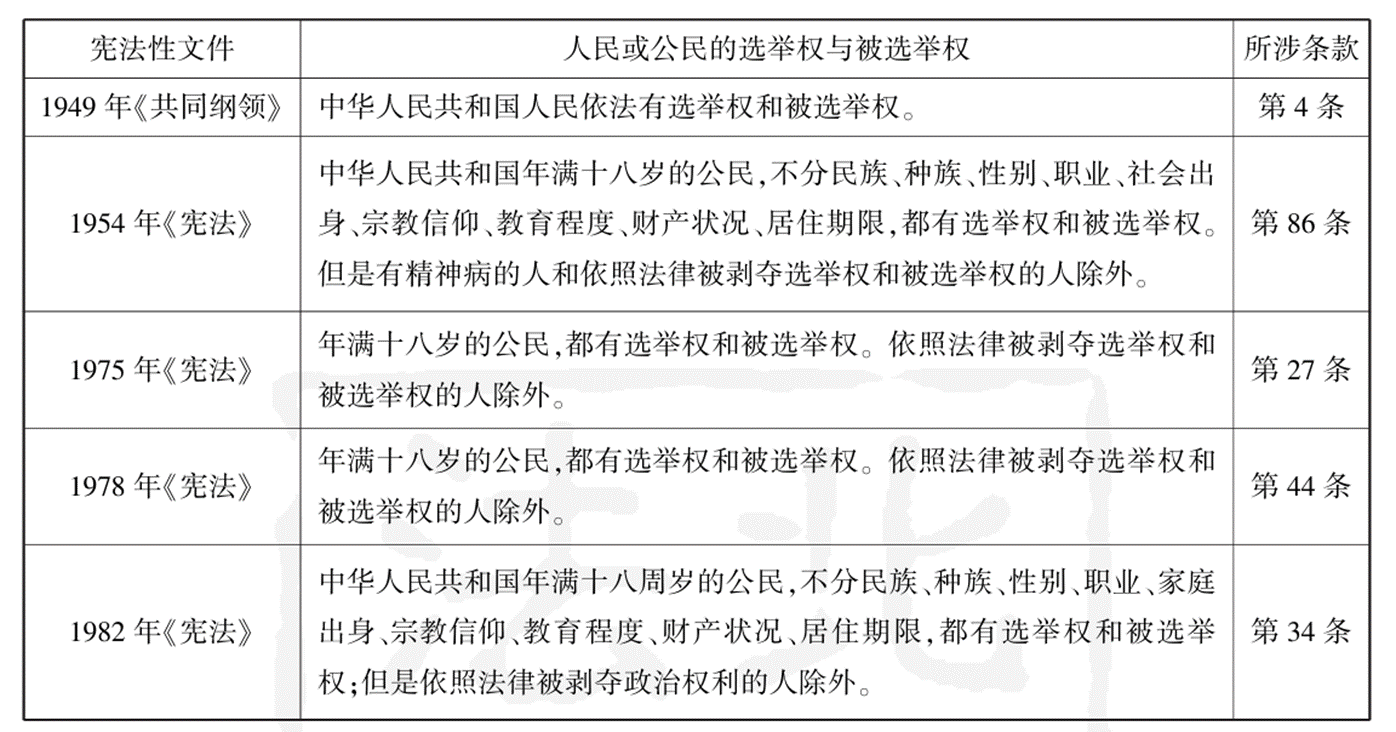
进一步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简称《选举法》)相关规定,可以更加直观地观察到“人民”的范围变化及其与民主政治权利的关系。根据1953年《选举法》第1条、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民族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33]凡年满十八周岁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分民族和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均有选举和被选举权,[34]但以下四类人员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尚未改变成份的地主阶级分子;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反革命分子;其他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精神病患者。[35]其后,1979年全面修订的《选举法》第3条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政治资格限定为“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者除外”。虽然其后经过1982年、1986年、1995年、2004年和2010年5次修改,但关于人民政治权利的限制规定没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选举权还存在停止行使和不行使的情形,该情形规定于198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根据《若干规定》,因反革命案或者其他严重刑事犯罪案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人,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在被羁押期间停止行使选举权利。其中,下列人员准予行使选举权利:①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没有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人;②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没有决定停止行使选举权利的;③正在被取保候审或者被监视居住的;④正在被劳动教养的;⑤正在受拘留处罚的。此外,《若干规定》还规定:“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行使选举权利。”
综上分析,作为“法上的人格”[36]的“人民”,其规范意义可通过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获得证立,并指向没有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所有公民。
2.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规范含义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为落实1954年《宪法》确立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宪法精神,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在现行1982年《宪法》中,“民主”一词共出现14次。其中,序言中出现9次,总纲中出现5次,涉及“民主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等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具体内容。而且,作为“体系化的规范群”,民主体现在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宪法制度体系中。[37]
对人民民主的含义解释,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人民民主就是“对人民实行民主”,[38]有的学者则认为“人民民主原则,即人民主权思想,核心是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改造后的且不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出现)中这一绝大多数群体中实行最广泛的民主”。[39]这些观点及其政治内涵解释虽然能够解释人民民主的政治含义,但严格说来,并不属于宪法学上的规范解释。按照前述“人民”的宪法学释义,“人民民主”的规范含义应指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的所有公民实行民主。根据现行《宪法》第3条第2款及第3款、序言第10自然段、第16条第2款、第17条第2款、第27条第2款、第67条第6项、第77条、第102条等的规定,其实现方式和手段包括民主选举、民主政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
(二)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含义
关于专政(Diktatur),据学者考证,在20世纪20年代初专政和独裁两词是通用的。“独裁”(Dukusai)是日语中的汉字,被用来翻译Autocracy、Despotism,后传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专政与独裁形成了表意上褒贬的分工。如在毛泽东那里,专政往往用来指革命政权的形式,独裁则用来形容反动势力。[40]另据考证,我国对Diktatur的翻译,来自于日文翻译及对马克思文章的直译,20世纪20年代对Diktatur的翻译源自日语混用的“独裁”与“专政”,在后续的发展中,才固定了“专政”的翻译。[41]在《辞海》一书中,“专政”一词被赋予两个含义:其一,“统治阶级依靠国家机器实行的统治。任何国家的实质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统治阶级凭借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贯彻本阶级的意志,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其二,“犹专权,独断行事”。[42]可见,现代汉语中的“专政”与中国古代汉语中的“专政”,含义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更加强调国家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更加强调国家机器的阶级统治及其方法。也即,专政包含有“阶级统治及其方法”在其中。这一“阶级统治及其方法”要求,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把代表机构变为“实干的”机构,把代议机构变成代表机关和工作机关,前苏联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和我国早期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这样一种实行“议行合一”的代议制;[43]在经济制度上主要是落实无产阶级经济平等权的目标,国家垄断经济,将利润统一收归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由国家统一分配;[44]在阶级斗争的手段上采用经济斗争(如罢工)、政治斗争(如游行、示威)、思想文化斗争。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专政”与“人民民主”的结合,不仅强调国家机器的统治及其方法,还强调国家政权的人民性。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运行的基本方式是:“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45]“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46]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解释中可以看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既包括人民民主的方式和手段,也包括专政的方式和手段(阶级统治及其方法)。
显然,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特别强调专政的方式和手段(阶级统治及其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人民民主与专政的结合,主要是通过落实人民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实现的。如果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实现方式和手段不能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政权组织形式(政体)落到实处,那就意味着国体与政体、人民民主与专政之间并不能融贯一致,除非两者间形成一种“手段”与“目标”的关系,也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形式,并消解掉外化于人民民主的专政方式和手段。因此,在规范意义上,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差别,是强调人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全体)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通过宪法明确规定的方式包括民主选举、民主政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目标。强调和明确这一点,对于明确人民民主和专政的规范关系,非常必要。
三、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价值定位
一般而言,一个概念的规范意义具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是指该概念的核心内涵,与含义具有大致相同的意蕴;二是指该概念的价值或作用。[47]由此,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意义体现为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在规范意义上存在的价值概念,而不仅是一个纯粹的“含义”或“事实描述”。通过前述国家性质的表述语、限定语辨析和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内涵解析可知,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规范价值主要集中在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问题。
(一)人民民主专政蕴含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式和手段问题
如前所述,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既包括人民民主的方式和手段,也包括专政的方式和手段。如所周知,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8]的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不再强调“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49],而是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纳入了“人民”的范围,强调人民民主的方式和手段问题。从不同时期宪法性文件中的规定可以看出其中的规范意义及其差异。1954年《宪法》规定明确规定,我国是一个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民主国家。但1975年和1978年《宪法》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取消了“人民民主专政”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前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规定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次宪法的修改强调了采纳何种手段或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但是,如果不考虑专政的手段或方式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就只是表达了无产阶级专享政权或者由无产阶级来主导组织政权,除非将专政的规范意义解释为一种带有方式和手段的国家治理模式。因为,如果说专政包含“实现方式和手段”的规范意义在其中,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在规范意义上,就既包含“人民民主”的方式和手段,也包含专政的方式和手段。也就是说,以人民民主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目标,要求国家通过一定的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以专政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目标,同样要求国家通过一定的专政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因此,在解释人民民主和专政的关系问题上,不能强调人民民主与专政的对立关系——把“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区隔起来,而应当强调人民民主和专政在方式和手段的统一。这一方式和手段的统一,如下文所述,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转变,通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实现的。
(二)人民民主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在方式和手段的侧重上存在差异
基于新中国成立后的5部宪法性文件的规定,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宪法实施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国体条款的不同规定反映了“人民民主”“专政”手段和方式的侧重。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方式和手段上的重大差别。而充分反映改革开放政策的1982年《宪法》,则对消除“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负面影响做出了重要的制度安排。1982年《宪法》重新回归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实际上回归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性质,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宏观上提供了政治空间。因为,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50]而现行《宪法》序言中“统一战线构成”的表述也被修改为“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51]。同时,“人民民主专政”中的关注点已经不在于“专政”,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也回归为“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这在事实上不再强调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手段。
需要特别指出,1982年《宪法》序言有如下表述:“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52]但很显然,宪法序言中的表述虽然体现了对专政方式——阶级斗争的肯定,但这里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53]如果结合现行1982年《宪法》序言最后自然段之“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表述,说明现行1982年《宪法》已然放弃了外化于民主法治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方式和手段,也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式和手段是一种建基于民主政治的法治方式和手段:“对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对敌对分子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对暴力恐怖活动,对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对残害生命和危害国家政权的邪教,对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等,我们必须依法坚决予以防范和打击,用人民民主专政来维护人民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54]
从宏观上来说,相较于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不再强调外化于民主法治的“阶级斗争”方式和手段。
(三)“三者有机统一”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方式
要实现人民民主和专政在方式和手段上的统一,解决国体和政体在实现方式和手段上的统一,除了必须摈弃外化于民主法治的阶级斗争方式和手段,还必须关注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涵。而依法治国是党实现对全体人民、各项事业有效领导的重要方式,党只有通过立法立规,才能对包括非党员在内的公民产生有效约束,真正实现领导。[55]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人民民主专政的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党的领导及其实现方式和手段,参见现行《宪法》第1条第2款;二是人民民主的方式和手段,包括民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见1982年《宪法》第2条、第3条和第4条;三是依法治国的方式和手段,参见现行《宪法》第5条第1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2款(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三种方式和手段贯穿于社会主义宪法的规范体系当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三者有机统一”之中。
1.“三者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三者有机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方式。“三者有机统一”的理论化表达最早由彭真提出。他指出:“在我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领导,遵从人民意志,严格依法办事,三者是一致的、统一的。”[56]该理论雏形体现了改革开放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斗争扩大化的反思。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认识的持续深化,党的十六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三者有机统一”理论,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57]可见,此时的“三者有机统一理论”标志着我国的国家治理开始走向法治化道路。2004年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对其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指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5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强调“三者有机统一”,该理论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指引作用更加突出。从理论目的来看,新时代的“三者有机统一”理论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三者有机统一”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承继性,但其主要目的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实现三者的深度融合和贯通。对此,韩大元指出:“新时代以来,宪法积极回应人民对民主发展的新要求、新期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拓宽民主途径,丰富民主形式,使中国的民主发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贴近人民的生活。在宪法轨道上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宪法对世界民主多样性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59]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来看,“三者有机统一”理论强调的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价值同源性和内在同一性。[60]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讲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61],学者们才会论证说“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62]。
2.“三者有机统一”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现执政方式和手段有机统一的关键
无论是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价值同源性和内在同一性,还是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在强调执政方式的贯通性和一致性,这为摈除外化于民主法治的阶级斗争方式和手段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曾对“三者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述和总体概括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社会主义法治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63]
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三者有机统一”理论的逻辑体系,回答了党、民、法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体现了“合法性与有效性”“民主与集中”“政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夯实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逻辑基础。有研究认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64]这种观点原则上是正确的,但也需注意,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都存在一定的实现方式和手段问题,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和手段,都是与“三者有机统一”理论不相符合的。因为,既然是“有机统一”,那么在理论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就不再是简单地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而是党的全面领导在依法治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而这意味着,“三者有机统一”不仅涉及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关切到三者在实现的方式和手段上如何各自和统一发挥作用的问题。
四、结语
2020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就包括坚持宪法确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不动摇,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65]正确认识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明晰不同国家性质在表述语和内涵上的差异,明确其蕴含的规范价值,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于坚持宪法确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不动摇,意义重大。
传统上,学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学理阐释,对其规范内涵和规范价值的阐释明显不足,忽视了不同国家性质在实现方式和手段上的差异以及实现方式和手段如何统一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全面实施宪法,必须重视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实现方式和手段上的作用发挥及其统一落到实处。希望这一研究,能够为中国自主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一定的学理助力。
【注释】
[1]习近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载《求知》2025年第2期,第6-7页。
[2]习近平:《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020年11月16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0页。
[3]这17部宪法性文件分别为《钦定宪法大纲》《重大信条十九条》《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天坛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训政纲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两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新中国颁行的四部《宪法》。
[4]《钦定宪法大纲》第1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5]如《中华民国宪法》(1923年)第1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统一民主国。”《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第1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
[6]1975年《宪法》第1条和1978年《宪法》第1条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7]1949年《共同纲领》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54年《宪法》序言第1段规定:“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1982年《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8]“实质上”应作如下解释:“实质上”主要是指三个方面,即在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和社会主义的前途上,“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致的。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9]参见刘山鹰:《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法重现——兼论82宪法第一条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载《探索》2013年第3期,第54页;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
[10]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所谓的阶级既指代财富不均的现象,即现实的阶级分层,更指代在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阶级存在的心理状态和社会需求。
[11]1954年《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12]See Mario Turchetti, “Despotism” and “Tyranny”: Unmaskinga Tenacious Confusion, 71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159, 159-182(2008).
[13]穗积八束在法政学意义上对国体和政体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国体和政体二元论。1910年,梁启超作《宪政浅说》,指“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又指“政体之区别,以直接机关之单复为标准。其仅有一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绝无制限者,谓之专制政体。其有两直接机关,而行使国权互相制限者,谓之立宪政体”。参见徐忱:《近代史上的国体政体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1日,第7版。
[1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15]同上注,毛泽东文,第677页。详细考证参见同前注[13],徐忱文。
[16][德]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页。
[17]周家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关系的探索》,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23年第6期,第58页。
[18]彭真:《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中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劳动节专号作》,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1日,第1版。
[19]同前注[9],韩大元书,第165页、第167页、第168页。
[20]宪法起草座谈会各组召集人联席会议的讨论(纪要)中有以下内容:对第1条,“归纳起来有3个意见:(1)主张在人民民主之下加‘专政’二字;(2)主张在‘人民民主国家’之上加‘多民族’三字;(3)地方上有的主张加‘团结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讨论结果:不改动。在《宪法草案》提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讨论中,代表们针对国体条款提出的具体修改意见为:“本条中如果写上‘共产党领导’,人民更明白,也更易接受;本条中可否把牧民写进去。因为只写工农,从文字上看,好像把牧民遗忘了;本条中的顿号可改为逗号。”同前注[9],韩大元书,第173页。
[21]参见同上注,韩大元书,第386页。
[22]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权性质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2页。
[23]参见同前注[17],周家彬文,第62-63页。
[24]1954年《宪法》序言第4自然段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1982年《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规定:“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已经结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将继续巩固和发展。”
[25]参见陈洪杰:《人民民主的宪法表达与主体性叙事》,载《甘肃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第172页。
[26]《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2条。
[27]参见杨陈:《论宪法中的人民概念》,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3期,第5页、第6页。
[28]参见同上注,杨陈文,第7页。
[29]这七种用法是:①历史上、文化上的共同体;②共和国的缔造者;③宪法的正当性来源;④国家权力的所有者;⑤宪法的遵守者;⑥政治意志的被代表者;⑦社会政策的对象。参见同上注,杨陈文,第8-9页。
[30]参见同上注,杨陈文,第10页。
[31]1982年《宪法》第34条。
[32]1954年《宪法》将有精神病的人和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放在一起,作为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例外规定,并不合适。因为精神病患者与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在行使选举权方面是有重要区别的,精神病患者有选举权,只是由于不能辨别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而不能行使选举权利,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是没有选举权的。因此1982年宪法对此作了修改。
[33]参见1953年《选举法》第1条。
[34]参见1953年《选举法》第4条。
[35]参见1953年《选举法》第5条。
[36]Etienne Balibar, What Makes a People a People? Rousseau and Kant, translated by Erin Post, in Mike Hill, Warren Montag, ed., Masses, Classes and Public Sphere, p.110.转引自同前注[27],杨陈文,第17页。
[37]韩大元:《论我国现行宪法的人民民主原则》,载《中国法学》2023年第1期,第25页、第34页、第39-40页。
[38]参见同前注[9],刘山鹰文,第61页。
[39]阳国利:《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宪法思想探析》,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16年第3期,第2页。
[40]参见褚宸舸:《“专政”与“宪政”》,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第51页。
[41]参见牟春伟、杜凤刚:《〈哥达纲领批判〉汉译本中“专政”概念考辨》,载《外语研究》2024年第41期,第87页。
[4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43]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
[44]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167页。
[45]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5页、第1475页。
[4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47]参见门中敬:《含义与意义:公共利益的宪法解释》,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4期,第153页。
[48][德]卡·马克思、[德]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49]同前注[16]。
[50]1982年《宪法》序言第8自然段。
[51]现行《宪法》序言第10自然段。
[52]1982年《宪法》序言第8自然段。
[5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4月3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2页。
[54]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年4月2日),载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
[55]参见郝铁川:《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理分析》,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第21页。
[56]彭真:《进一步实施宪法,严格按照宪法办事》(1983年12月3日),载《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9页。
[57]江泽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8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58]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9月15日)》,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59]同前注[37],韩大元文,第25页。
[60]参见汪习根:《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时代精神》,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32页。
[6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62]吴跃东、程水栋:《党的领导与全面依法治国内在关系研究》,载《思想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第36页。
[63]习近平:《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2015年2月2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页。
[64]参见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载《经济日报》2019年11月12日,第12版。
[65]习近平:《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2020年11月16日),载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91页。

